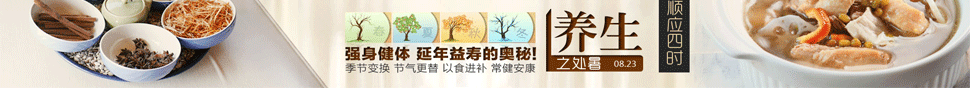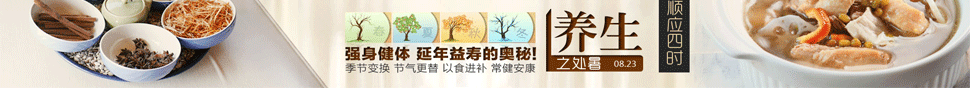轻音缭绕,茶香满室,草帘隔断了一张和另一张古朴木台的联系,却让围坐木台前品茶的人在帘缝的隐约间发现彼此的志趣。阳光斜洒,透过木质窗棂格,落在泡茶女子灵动飞舞的玉手上,仿若给了她们手中那一杯杯茗茶别样的仙气。冬尾的一个午后,和三两老友走进了一家位于“地下”的茶室。或许是文化人“大隐隐于市”的心性修炼使然,这间茶室的创始人选择了位于地下的人防工程闲置空间开辟这方城市净土。茶室浅于地面,其上又有绿植掩映入口,从一侧道路上经过,似乎根本找不到它的踪迹。也因此,它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城市繁华中,躲去了几分城市的喧闹与叨扰,似一个隐匿在闹市中的清幽之地,替人们收藏好了一份触摸历史与人生的清静,只待来客在此感受茶香中的时光停留。茶室里的人不多,有独坐一杯绿茶前,斜看远处云卷云舒者;也有与茶艺师对坐相谈,品茗论道甚欢者;还有似我们一般围坐一处,或聊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或不说话只饮着自己杯中的茶水,感受着时间点滴而过者。我其实,算不上一个懂茶之人。与身边熟读《茶经》兼修茶道的友人相比,我对茶叶知之甚少。我总觉得喝茶品茗本就是一个磨人心性的活动,能够耐着性子熟悉各种茶叶、掌握各种适宜水温、品出各种茗香的人,骨子里总是会更多一点儿温润厚重之气。这种气息可能是茶作为现实和历史的交错的载体,让文化与人生浸染于一人之身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我是爱茶的,虽然我熟悉且偏爱的茶很少。在我熟悉且偏爱的为数不多的茶之中,竹叶青是其中一种。我极喜欢那茶叶在水中晕开之后所散发出来的香气,那样清而不淡的味道,总能让我平静地与自己相处、对话、然后淡忘应该忘掉的人与事。喝茶,其实还有一个妙处,若你想讲规矩,那各种茶理、茶道足可把你逼成学究;若你不想讲那些劳什子的规矩方圆,那不论何时何地,你都能一解茶馋。须知,林下烹茶味亦禅。譬如我喝过最有趣的茶,其实还不是在这藏于“地下”的茶室里,而是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大漠中。几年前,作为背包客,和好友进入了甘肃临夏附近的沙漠中。我们并非一群想要挑战生命极限的人,只是想感受不同的生命状态。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去创造和享受荒漠中的舒适。于是,我们在一寸空间一寸金的行囊中,放入了茶叶和野外专用的烧水泡茶的壶。那天夜里,经过一整天徒步行走的我们,在寻到一处可安营扎寨之地后,便从齐人高的背包里掏出帐篷、充气床垫、羽绒睡袋等等生存必备物品,收拾妥当。随后,我们围坐在一起,生火、架起烧水壶、掏出一小袋竹叶青,待那一根根嫩绿的小芽在各色器皿中树立起来,那一阵阵让人思绪飞扬的茶香在这塞外之地肆意飘溢,一群原本嘶哑的声音也逐渐开始有了生气——这产自峨眉山的茶叶,不仅用茶香缓解了我们的疲劳,也用茶香给予了我们故土的力量。那个在大漠里的夜很冷,我坐在一根枯树枝上,端着茶汤,仰望着城市里已不能再见的星空,在悠长的茶韵中,只是沉醉。大音希声,道隐无名,一盏清茶里便有四季,有人生,还有世相百态。若愿意,甚可见儒释道,这便是饮茶的趣味。最近两三年,生活更趋安定,那个巨大的背包已有了厚厚的灰尘,我也再没有过野外喝茶的经历。但我坐在这茶室里,看着手中的茶杯,脑子里天马行空胡乱地冒出各种不被人打扰的想法和年头,茶杯里泡得正好的竹叶青茶芽在嫩绿清明的汤色中直立着,也觉得甚是好看的。赵琨(作家)(赵琨,笔名荞麦花开,长于古典文学的鉴赏和评论,《红楼梦》文本研究员,即将出版《大河向东流》、《陈道明的表演世界》等著作。)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biyadia.com/bydyw/132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