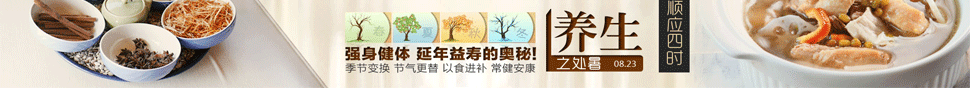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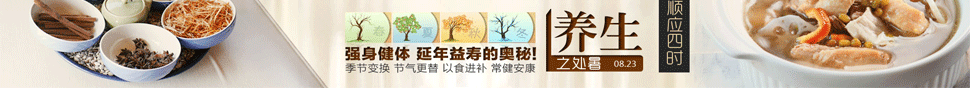
竹子骨格清奇、刚直不阿,而茶质朴淡泊、清白可人,故历代文人爱竹也爱茶,且常常茶竹并称。
唐人认为茶种“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竹间茶最佳。联云:“山间竹里人家,清香嫩蕊黄芽。又有联云:“莫干清凉世界,竹荫十里香茶。“春自山中采,香宜竹里煎。”竹里茶是否真的品质超群呢?实在寻不出多少科学依据,其实是文化人主观世界的外化,心内理念的物化。爱竹及茶,爱茶及竹,竹香茶亦香,竹高洁茶亦高洁,人与茶、竹结友,可与之作心灵的交流。观其竹,品其茶,心中的浩然正气便有了寄托。
唐代诗人姚合“竹里延清友,迎风坐夕阳(《品茗诗》)。“清友是茶的别称。竹里品茶并陶醉于美好的大自然之中,古人视此为雅事,称之为“林下之风。
宋人亦喜欢竹里煎茶,北宋诗人王令(——),字领美,广陵(今扬州)人。他与王安石是“两挑担(二人之妻是姐妹关系,姓吴)。其《谢张和仲惠宝云茶》诗云:
故人有意真怜我,灵荈封题寄荜门。
与疗文园消渴病,还招楚客独醒魂。
烹来似带吴云脚,摘处应无谷雨痕。
果肯同赏竹林下,寒泉犹有惠山存。
诗人获得了张和仲赠送的宝云茶,其茶采于谷雨前,叶嫩,可煎出浓浓的茶汤,便邀朋友作林下之游,在竹里煎茶,并声言他存有惠山泉水。
宋代理学家朱熹爱茶也爱竹,有诗云:“客来莫嫌茶当酒,山居偏与竹为邻。他发现竹子长势迅捷,欲悟其奥妙,便“静观守竹,将竹与哲学联系在一起。古代茶人多如朱熹,凡事喜欢琢磨,琢磨就是“静而后“悟,“守竹如此,“品茗也是如此。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在《斗茶檄》中说:“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犹竹庶可齐名。他认为茶、竹可齐名并称。《茶疏》中载“明窗净几,轻阴微雨,茂林修竹,清幽寺观”。
明代诗人陆容《送茶》云:
江南风致说僧家,
石上清香竹里茶。
法藏明僧知更好,
香烟茶晕满袈裟。
这首诗赞扬僧家茶事最具“江南风致”,“风致”何在?不外乎是“竹里煎茶”。
清人郑板桥(—),名燮,板桥为其号。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板桥画竹与品茗同样闻名,他作一妙联云: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
另有画题诗云:
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
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山。
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起间。
《题画》一文中云:
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
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一作),名沾,雪芹为其号。他在《红楼梦》一书中多次茶、竹并称,如该书第十七回《题大观园诸景对额》中,贾宝玉给“千百竿竹掩映”的潇湘馆题联是: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生凉。
这些翠竹如林黛玉题诗所云“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竹里煎茶连茶烟也带绿意和凉意。
诸如竹林种茶、竹里煎茶,让竹子在其中充当角色,除了表达古代士子对“茶品、“人品的追求外,从审美上讲是体现“以淡为宗的旨趣。竹叶入药称“淡竹叶,其味甘淡;竹子简而力,入画疏疏落落,便于“计黑当白。中唐之后,禅宗兴起,文士在茶与竹中获得禅趣。特别是明代引禅入画,“淡泊成了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画竹品茶、竹里煎茶最便于文人体悟这种艺术境界。
清代文人爱竹大约还有一个原由:明亡于清,满人入主中原,遭到了许多文人学士的坚决反抗,或举兵反清复明,或归隐山林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清初的统治者,一方面加快满族汉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对不屈服的士子采取怀柔政策。当时的士子们,既觉复明无望,臣服又不甘心,基于对大明王朝的“恋母情结使然,关于“气节的说法普遍见于文士的诗文和言谈中。当他们拖着猪尾巴似的长辫子沉醉于画竹、写竹或竹里煎茶时,不正是那已淡忘的“气节观的曲折反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