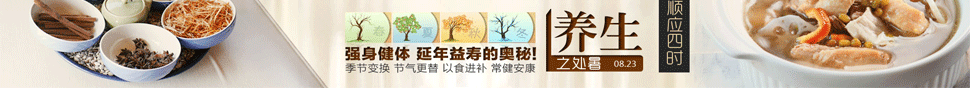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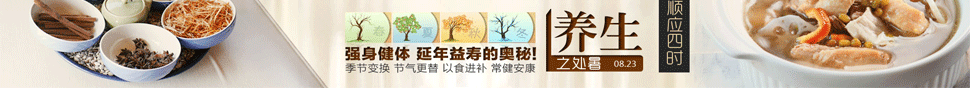
尚纯江
“高粱”
小时候,田里的“大个子”庄稼就数高粱了。秋天一到,高粱构成的青纱帐无边无际,在秋风里沙沙作响。高粱穗儿勾着头,像害羞的少女,脸涨得红彤彤的,在风里扭动着腰肢。放眼望去,葱郁的青纱帐舞动着红红的云彩。秋风吹过,空气中弥漫着高粱气息,甜甜的、诱人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吸一口气,醉人的清香涨满肺腑。
小时候,家乡种的多是春高粱。春高粱高高的杆,红穗儿在风中摇曳,很好看,产量却很低,只有百把斤。后来改种夏高粱,夏高粱是新品种,低杆高产。75年,我村成为县良种种植点,种了近三百亩的夏高粱。夏高粱成熟季节,粗壮的高粱杆顶着硕大饱满的穗儿,吸引了一群又一群的鸟类(麻雀等)。人们在高粱地里竖起很多草人吓唬鸟类。但鸟类对草人置之不理,反而飞到草人的头上跳来跳去。看庄稼的人挥动着树枝大声驱赶,一片片黑压压的鸟群飞去,又一片片黑压压的鸟群飞来。我们村被一片片红云彩包围着,被甜甜的清香包围着,也被唧唧喳喳的鸟群包围着。此刻,大人的一颗心也被丰收的喜悦包围着。高粱的丰收,像高粱酿造的美酒,醉了一颗颗农民的心。
春种秋收。秋天,是收获希望的季节。收割高粱的时候,大人们挥汗如雨,忙着收割。我们小孩子奔跑在田野里,逮蚂蚱,逮蚰子,逮蛐蛐,摘田里的香麻泡吃。还用秫秸扎蚰笼子,把逮到的蚰子装进笼子里,蚰子在里面快活的鸣叫着。
有着“五谷之精、百谷之长”盛誉的红高粱,是黄淮以北地区的主要粮食。因为产量低,除去公粮,分的高粱很少。娘总是抓一把高粱面和豆面掺进红薯面做面条。掺高粱面的面条劲道润滑、清香可口。丰收了的75年,是个肥年。年底,家家都分了几斤高粱酿造的酒。父亲说,高粱酿造的酒,清澈甘冽,酒味浓香。往年,我们分的是红薯干酿造的白干酒,白干酒浑浊而略带苦味儿。
在我的记忆里,不但掺高粱面做的杂面条好吃,娘用高粱面做的面鱼儿(娃娃鱼)也好吃。娘拿一把漏勺把高粱面熬成的热粥漏到凉水里,粥遇冷凝固,就成了一条条“小鱼儿”。把面鱼儿放进凉开水里,放进盐及高粱醋,滴几滴小磨香油,一碗清香可口润滑无比的面鱼儿就成了。那时,只要娘做面鱼儿,我的小肚子准会变得溜圆溜圆的。现在的街头,我也常见到面鱼儿,但那面鱼儿不是高粱面做的,是用淀粉做的。淀粉做的面鱼儿,当然没有高粱面那特有的清香。
高粱在我们家乡,叫蜀黍或秫秫。蜀黍,一年生禾本科植物,在我国种植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本草纲目》说,“蜀黍北地种之,以备粮却,余及牛马,盖栽培已有四千九百年”。现有出土的高粱实物加以验证。高粱性温、甘,可燥痰祛湿,宁心安神;富含钙、磷、铁、蛋白质、粗纤维等营养元素。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高粱不仅是我们家乡的主要食物,而且是酿酒的上好原料。我们家乡盛产美酒。宋河粮液,是享誉全国的全国名酒,其主要原料就是高粱。国酒茅台、汾酒,泸州特曲、竹叶青及台湾金门红高粱,其主要原料也是高粱。
高粱遍身是宝。高粱杆(秫秸)是我们家乡做箔的最佳原料。我家的房箔子(房隔山)以及晒东西的箔都是用秫秸织的。秫秸梃子可以做锅排(锅盖)。我现在的家中就有这样一个锅排。过年包饺子时,用来放饺子。秫秸皮可以做席子,红秸皮和白秸皮编的席子红白相间,很是好看。古人爱席地而坐,坐的席子,恐是这种席子吧。秫秫茆子可以做条帚,高粱壳也可以用来酿醋,醋糟是喂猪的好饲料。
高粱有很多用处,也有很多故事。莫言的家乡有很多红高粱,漫野里的红高粱使莫言聚集了太多的情感,使他写了很多红高粱的故事。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拍成电影,一举成名,享誉中外。莫言此后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想与红高粱不无关系吧。
红高粱作为我们家乡的主要农作物,现已见不到了。高粱产量低,是粗粮,经济价值不高。二十多年来,人们放弃了种植高粱。东北等一些地区还种植高粱,大概是因为酒的缘故。没有了红高粱,酒就没有了酒香味。酒,是红高粱存在的理由。而我,却在红高粱远去的时候保留了一份红高粱的情愫。这种情感,与娘的面鱼儿杂面条一样沉淀在记忆的深处。
“茭草”
在我们家乡,草高粱不叫草高粱,叫“茭草”。草高粱之所以被乡人称为“茭草”,实在是误会。那种叫做茭草的植物,其根茎叫做茭白,是一种江南蔬菜。而家乡种植的“茭草”——草高粱,是一种饲料。同叫茭草,却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们家乡,种红高粱,也种茭草(草高粱)。茭草是快牲口的上乘饲料。我村有几匹快牲口。快牲口是指马和骡子,干起活来很快,一匹马顶两头牛。干活多,生活待遇自然就好些,而“茭草”嫩绿多汁,营养丰富,味甜香,适口性好,是牲口们的美味佳肴。
从我记事起,我村就种有很多“茭草”。西边太平沟的堤岸上、河漫坡里,及一些贫瘠或盐碱地里都种着茭草。因为“茭草”不仅可以做青饲料,还可以做干饲料。其秸秆含糖量高达(BX),茎叶鲜嫩,植株含粗蛋白15.29%,鲜草含粗蛋白3%,营养价值很高。
“茭草”——草高粱是一年生禾本科牧草,像家乡的父老乡亲一样,生存能力很强,耐得住贫瘠。春暮时节,在那些盐碱地、易涝地、旱垡地或低洼地里播下种子,就能生根发芽,长出一片绿色来。其抗旱、耐涝、耐瘠薄和耐盐碱性较强。干旱时,其他庄稼像霜打的茄子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枯萎了枝叶,而漫河坡的“茭草”此时却生机盎然,葳蕤成一片浓郁的绿色。风一吹,绿色的草高粱婆娑起舞,碧“波”荡漾。水涝时,淅沥沥的绵绵细雨把农村的世界变成汪洋一片。那些不耐涝的庄稼在水中奄奄一息,而此时“茭草”像芦苇一样在水中摇曳生姿。
“茭草”——草高粱和红高粱是一个家族。其叶、秸茎、种穗、籽粒等均与高粱相仿。只是叶子小一些,杆细一些,穗子小一些,籽粒也小些,“个子”也矮,是缩小版的高粱。
“茭草”生存能力强,其再生能力也很强。“茭草”刈割后,再生速度快,一年可刈割4次。所以,作为牲口的饲料,在我们村广为种植,河岸及沟叉处的贫瘠地里,都种有“茭草”。
“茭草”之所以生存能力强,再生能力强,与“茭草”的根系发达有关。“茭草”的根系如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密密麻麻,深及黄泉。鉴于其发达的根系,村里盖房子用的土坯有一部分就是在收割“茭草”后犁制的土坯。其方法是:“茭草”收割后,把茬地整平,用石磙碾压结实;用犁坯专用的犁子,按照垒墙所用坯的大小、厚度犁成长方形,再用犁铲把坯从底层铲下来
犁坯不仅要用工夫,最重要的是技术。没有一定技术是犁不出土坯来的。
适者生存。这里的适者,并不是其本身适应生存的能力,而是现实生活中是否需要这种植物。实行了机械化以来,牲口逐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而作为牲口饲料的“茭草”也渐渐成为永久的记忆。现在,如果你问年轻人啥是“茭草”?他们可能会说,是那长茭白的茭草吗?或者他们摇摇头。因为他们可能吃过茭白,或者根本不知道那种叫做“茭草”的草高粱。
淮草
在过去,县城有城墙,城墙的外围有护城河;村寨有寨墙,外围有寨海子。尚桥是我的家乡,是个不能再小的小村庄,只有三四十户人家。村庄虽小,却也五脏俱全,围绕着村庄有一条浅浅的海子。越过海子,就是淮草地了。对于村外的那片淮草地,我一直保留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淮草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生命力极其顽强。在寒冷的冬天,荆棘遍布的淮草地光秃秃的一片。但春天一到,万物复苏,淮草地便“春风吹又生”,尖尖的、嫩绿的淮草芽与茅草一起露出了地面。在春风春雨细心的呵护下,淮草们渐渐长高,深可齐胸。葳蕤的淮草和那些杂树一起,在村外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这屏障像绿色的海洋在风中微波荡漾。儿时,这里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我们头戴着柳条帽手持着木头手枪,像邱少云那样静静地埋伏在这里,玩捉鬼子、抓特务的游戏。有时,我们也会通过这道绿色屏障,悄悄地进入生产队的瓜园,偷王海瓜吃。
一到秋雨连绵的季节,淮草地里便长满了一种叫做地鸡蛋皮的东西。地鸡蛋皮属真菌类,薄薄的、滑滑的,泛出嫩嫩的墨绿色,极富营养。雨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们便疯了似的满地里捡地鸡蛋皮,把淮草践踏得一塌糊涂。大人们见到此情景会发出叹息:可惜了这片淮草了。但那时地鸡蛋皮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餐桌上的美味,特别是地鸡蛋皮下到用红薯面擀成的面条里,吃起来滑滑的、嫩嫩的,带有淮草香味,好吃极了!在我们眼里,为了采摘地鸡蛋皮,就是踩倒了淮草也没有什么。
淮草是野生的。在我们村外,有大片大片的淮草地。一到秋季,淮草的樱穗如芦花一样随风飘荡、起舞。淮草丛中夹杂着白杨、刺槐、野杏树、桃树、苦楝树、椿树等各种树木。草丛隐藏着云雀、麻雀等鸟儿的巢或者野兔的穴。一阵风吹过,叶儿或草发出“沙沙”的声响,鸟儿们即兴“唧唧喳喳”地唱。雨后,蝉鸣蛙鼓,蜻蜓在草间自由自在地飞,抑或悠闲地停在草上或小树上歇息。不上学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爬树、捉蜻蜓、捕蝉、捕蝴蝶、捉迷藏。有时,我们也在草丛中寻觅鸟蛋或者蘑菇、木耳,摘些野生的桃、杏,改善家中的生活。那里,让人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很快便被收割淮草的人们弄没了。在那个年代,淮草是每家每户盖房子的材料。那时房子都是茅草房,屋顶上缮的是淮草。人们喜欢淮草,不仅仅是因为淮草结实耐沤,做房顶寿命长,更重要的是淮草是野生的,不需支付任何成本,有力气收割就是了。所以淮草收割的季节,村民们挥汗如雨,挥舞着镰刀抢割。即使不盖房的人家,也赶着收割些淮草,用作生火做饭的燃料。
改革开放之后,淮草地便被分给每户人家。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这片荒地被开垦出来,成为人们的粮仓。淮草地不再存在,地鸡蛋皮也不再存在,鸟儿兔儿也离开村庄远去。富足起来的村民住上了楼房,淮草房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成为遥远的过去。淮草,也在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
近日,我在百度搜索一下,淮草只有一个名词解释,“淮草:别名又叫野古草、田草、迭茅草、野罐草、麦穗草等,为禾本科植物,有清热凉血的功效等”。简短的几条信息说明,淮草只是一种野草罢了。在人们住在茅草房里的时候,野生的淮草还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随着生活的改善及富足,茅草房早已成为记忆,淮草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所以,淮草也已成为一种淡淡的记忆。
青麻
青麻,一年生亚灌木状草本植物,亦称野苎麻或苘麻。我国种麻已有多年的历史。《诗·陈风·东门之池》中说“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诗经》中的东门就是陈都宛丘(淮阳)的东门。《易·系辞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以书为契”。绳结而治,绳从哪里来?种麻沤麻,搓绳。斯时之麻,乃苘麻(青麻)也。
《本草纲目》云:苘麻,今之白麻也,多生卑湿处,人亦种之。叶大如桐叶,团而有尖,六、七月开黄花,结实如半磨形,有齿,嫩青,老黑,中子扁黑,状如黄葵子子,其茎轻虚洁白,北人取皮作麻。其嫩子。小儿亦食之。
鹿邑古称苦县,虽不属陈而属楚,但与宛丘却相距不远。想来那时的鹿邑也是“用池沤麻”的。从我记事时起,家乡太平沟的漫河坡里就有一片片的青麻地。夏天,一人多高的青麻绿油油的一片。高大茂密的青麻枝叶相连,密不透风。那时,我们小孩子常常把衣服脱了个精光,溜进太平沟里洗澡、捕鱼、捕虾、抓青蛙。然后上岸,扯几片麻叶,裹着小鱼烧鱼或青蛙吃。此时,青麻结出了一颗颗果实,果实“如半磨形,有齿,嫩青”。这种嫩嫩的果实我们管它叫麻梭子,其味道略带一种清香的甜。麻叶烧小鱼,就麻梭子吃,也是一种美味。
在我们家乡,不但种青麻,还种黄麻。黄麻也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秆高大且直,不枝不蔓,可以密植。椭圆形的黄麻叶边沿锯齿状,钻进麻地割草时,麻叶常划破胳膊,火辣辣的疼。黄麻开着紫色或白色花蕊,很是好看。
青麻成活率很高。清明过后,在地里撒上些青麻籽就可以了;黄麻种子小,顶土能力弱,播种时土壤墒情要好,要按田畦种植。春风吹过,青麻(黄麻)苗见风长,春暮时分,已是绿油油的一片。入夏时,青麻(黄麻)便已长成一人多高。
种麻简单,重要的是沤麻。收割下来的青麻(黄麻)硬硬的外皮含有很多胶质成分,不经沤制是搓不成麻绳的。
沤麻要选个开阔的水面。我们村有两个水坑,一个在村的西南角,与太平沟相通;一个在村子中间,坑旁有一口水井,水井旁竖有一个碌碌,我们村都吃这口井里的水。所以,我们村沤麻一般都在西南角的那个大坑。大坑直径约40多米,水很深。
沤麻时,队长挑选几个身体好、水性好的男劳力,把捆好的麻棵拉到坑边,排成一排,放到水里,一层一层码好踩实,最后在麻排上压上厚厚的一层泥土,再用草绳捆绑在木桩上固定,不让麻排浮起来。约过了两三天,大坑的水开始冒泡,水面浮出一块块绿沫,散发出呛鼻的臭味,野生的鱼儿开始翻坑,一条条鱼儿亮起白白的肚皮“仰泳”。此时,我们管不得水中的臭味,开始捞鱼。捞出来的鱼儿洗干净后一点臭味儿也没有,娘给我们炸的小鱼儿很好吃。
沤麻的时间很有讲究。沤过了,麻皮脱“裤子”,麻芘子不结实;沤的时间短了,麻皮发硬,搓的绳不结实且不耐用。所以,沤麻是有些技术含量的活儿,需好把式才行。
沤过的麻经过脱皮晾晒后就成了可以搓绳的麻。此时的麻白白亮亮的,有一种清香。过去,生产队沤出来的麻一部分留作自用,一部分卖给供销社。
生产队解体之后,我们家乡就不再种麻,人们使用绳子就直接到市场上去卖。尼龙绳问世以来,麻绳越来越少。但尼龙绳捆东西时滑不溜湫的,捆不结实。这时,人们会叹一口气,说,捆东西啊,还是麻绳结实。语气里,含有些许伤感或者怀旧的意味。
近日,我在涡河岸边散步时,看到几棵苘麻在风中摇曳,便摘了一颗嫩嫩的苘麻果(麻梭子)撂在嘴里,一股久违的、略带甜味的清香便弥漫心间;往事,像一首歌久久在心头回响。
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