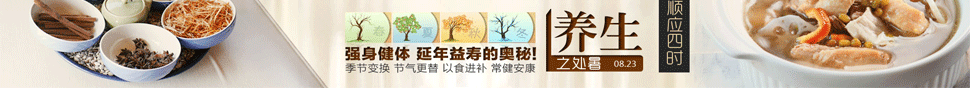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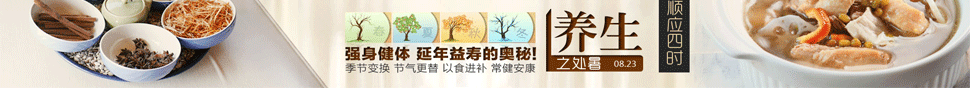
浮生·盛世蚁族
傅春桂
补锅匠老陈
老陈其实不老,五十来岁,却长出一副略显老成的面孔,缺了一颗门牙还嘴巴子多,爱说,也挺能说,若让他停下不说话,像谁欠了他的钱,只要让他说话,便眉飞色舞起来,快活得忘了时辰,忘了忧愁。
我本不认识老陈,只看到他隔三差五的周期来小区摆上他的修补工具,不一会就有一些老人拿了自家的高压锅或电炉锅来找老陈修补。老陈不慌不忙接下,仔细看了看,敲了又敲,或取下某个零件放在嘴里吹了又吹,这才抬头说多少钱,修就放下,几点来取。老人们讨价,老陈低头做他的活,说不能少了。见状,老人们不再纠缠价格,只说活要做好,老陈说这个是当然。
某个周末,我在家看NBA,老婆大人打电话要我送家里的两个高压锅下去。我不想下去,老婆说她要外出,没时间等,钱已经付了。看完球赛后,我急匆匆赶到老陈的修补点,老陈不乐意了,数落起我来。老陈说:你这个同志,误了我的工夫不说,也枉费了你当家的心意,我要是收了钱走人,你找哪个去?我知道老陈不会走,却故意逗他:你经常收了人家的钱就跑路?老陈说:看人来,像你,不跑还等你?
老陈放下手中的活,慢条斯理检查我的锅子,认真又细致,锅盖处有一凹陷,他找了木榔头,又找了一处台阶,在上面敲打起来,直到他满意了,才拖沓着走过来。正是夏天,他上身穿一件有点破旧的汗衫,因有些年份了,汗衫上有些洞,一些地方还脱线了,露出脊背。下身则穿一条宽松的旧军裤,是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兵时穿过的那种,现在难得找到了。裤腿是往上绾着的,只见两条腿上全是溃烂的疤痕,有脓水不断流出,老陈一会用手去抹,一会又从塑料袋里取出手纸,很有经验的擦拭着。
老陈在做这些时,还不时要告诉我如何保养锅子的窍诀,我没听进去,只想着他手上的脏东西会弄到我的锅子上,心里不免有些悻悻的。老陈要我有事就去忙,一小时后来取。我没有走开,问起他的脚是怎么了。老陈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说到糖尿病,我多少有点常识,我多个同事患有这种病,保养不好,会并发综合症,很危险的。我问老陈为什么不去住院治疗,老陈说我一个修锅的,医院?我说总不能就这样下去,要是不治……老陈打断我的话,说死是吧。我没做声,老陈笑呵呵说:早想好了,买一包药,找一个深山,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
我莫名的心悸,沉沉的半天不说一句话。老陈看出了我的心境,对我说:我想得通,人嘛,就是一死,只要不磨自己,也不磨别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老陈从更大的尼龙袋里找出一张报纸要我坐下,这才发现,他的身后摆了四五个这种尼龙袋,里面都是装得满满的。我问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袋子,他说这是他的全部家当。
我并不想坐,没有接老陈的报纸。这是一张本市办的省报,以前有副刊时,我是看的,取消了副刊后,我不再看了。老陈开玩笑说:你这个人不爱学习,没有文化,没文化是可怕的,什么事都不晓得。然后他讲了报纸上登载的一些事情:前天晚上,就在前面XX小区,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喝了酒,从五楼跳下去,死了。晓得他为什么要跳吗?我摇摇头。老陈说:说你没文化,你还不服。翻着报纸说:看看,看看,肝癌,没钱治,不想给家人添负担,跳了楼。到头还是害了家人,要我,跳海,被浪卷走了,省事。说完这件事,老陈又说了一些别的事,也是从报上看到的,都是一些底层人的凄惨事。
老陈细细做着事,我发现他做事非常负责任,锅子上有些污渍,他找出钢丝球用力搓,直到他认为干净了;锅子的边缘有些歪了,他找出专用的钢套塞进去,拿了铁锤很有分寸的敲打;只要某个地方有点问题,他都会小心翼翼的做到位。然后很随意的告诉我说这是他师父教的,做事用心,做人实在。随后叹息一声说:没人学,要带到土里去了。我说教会你的崽女嘛。老陈说他们哪看得上这手艺。他说他曾经带个一个徒弟,坐不住,跟了半个月跑了。
我突然对老陈有了好感,也产生好奇。在和老陈的交谈中,我知道他是长沙县跳马镇的,有老婆,因为这病,他和老婆离婚了,房子给了老婆,自己一个人出来荡,后来碰到了他师父,才学了这个。老陈有一个女儿就住在这个城市里,但他从来没有去找过。有一个儿子,分开过了,房子归了他。老陈出来二十多年了,一直在这一带做修补,他蹲守的点有十来个,每个点做一天,生意忙不过来时会多留一天,轮换。他说客人很信任他,等都要等到他去。他还透露了他的收入,这个数字是我收入的N倍。我说你既然有这样高的收入,为什么不去看病?他说不是没有去看,是看不起,他说住几天院,他几个月的收入就没了。还说真要是住院了,收入就断了。他明白这病也是看不好的,干脆不看了。我问他崽女们难道不管吗?他说:我给不了崽女什么,也不能给他们添累。我问为什么不去找女儿?他说女儿活在城里,更难。
老陈在城里没有租房,他是做到哪个点,就在哪个点的桥下或门铺下睡一晚,那几个尼龙袋里的东西就是他的被褥和衣服等七七八八。我想象不出他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心一阵紧似一阵,对这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人怜悯起来。我说你这样子居无定所,对你的病不利。他说:就是往那条路上去的人,不怕。我说你有收入,为什么不租一个固定的地方?他说他要管这么一大片地,方圆一二十里,路上耽误的时间长了,不要做生意了。我问他晚上怎样过,他没有明白,说睡在桥洞里,人行通道里。我没让他继续说,问他睡觉前的时间怎样打发。他说有时去小区里打打牌,有时和人喝酒聊天。我惊诧,问他还打牌喝酒?他说过一天快活一天,只要不死,这酒和牌是戒不了了。
老陈抽烟,本来我不抽的,因为前一天去看望战友,随手装了包烟在口袋。我给了老陈一支,他用油纸擦干净手,接了烟说我的锅还有几处要换东西,我说换,把一包烟给了他。老陈不肯接,我丢在他的塑料袋里,老陈不忘挤兑我几句。随后说换的话要加多少钱,我说加。老陈细细摸摸的弄了一个多小时,认为满意了,才将锅子原封装好交给我。
这之后,只要看到老陈出现在那里,我都会过去打声招呼,老陈还是拿话埋汰我,说最近又发生了许多事,你这个不爱读书的,天下发生的事都不晓得。我说你脚还那样,他就说要死了,快了。当看到他脚好些时,我说好多了。他说这回又死不了了。我劝他少喝点酒,他说不让他喝酒才要他命。
慢慢的,一年过去了,我和老陈竟然成了老熟人,只要见了我,他老远会打招呼:不读书的,过来,我讲故事给你听。我会笑笑,顺从的走过去,和他闲聊几句。当我有什么好的东西在手上,会送些给他,只要他出现在我的小区,我也会有心去买一份米粉或盖码饭送他,后来,来了一个流浪的疯子,多少还有点清白,两人搭起了伴,小瓶子酒摆在了摊子前,他会把饭分一半给那流浪汉吃。后来我买双份,老陈就不再要我买了。
今年,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老陈出现,我竟有点空落落的,才发现,我心里装下了这个老陈。我上下班本来是不走老陈摆摊的门进院子的,却总要绕过去看看。大约三个月后,老陈来了,他正低头做活,我看到了,竟然小跑过去,在他面前“喂”了一声。老陈抬起头来,不慌不忙说:不读书的,到阎王那里走了一趟,说我“难”没有受够,不收。我弯腰去提他的裤腿,老陈并不制止,只说:又死不了了。
我眼有点发热,说你这个老陈。
湘乡补鞋匠
选择让邓师傅来给我小孩的鞋做修补,是看他的补鞋机上挂了一个小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给鞋子美容吗,找我错不了。后面是名字邓XX,名字前还加了个头衔:八级工。
鞋子是靴子,小孩子参加工作第一次领薪水时买的,他自己一双,送我一双。他因天天在工地上跑,鞋尖的地方有点脱胶,小伙子爱美,要我帮他去弄弄。找了几家上档次的修鞋店,嫌麻烦,都不接,却告诉我去某某街面找修补的师傅看看。
这一片正在搞改造,到处堆满了垃圾,车子一过,灰尘扬起来有三层楼高。邓师傅的摊子摆在一棵银杏树下,树上的杏叶不多了,树下却是满地鹅黄的银杏叶,犹如天空散落的一片黄金雨,杂乱无章地遗落在哪里,让我想起了一位文友说的:像锦鲤的鳞。
一眼就发现了修补的摊子,摊子前摆了五六只鞋,旁边有一辆破旧的脚踏三轮车,车里有纸箱,啤酒瓶,破铜烂铁。一条马扎静静立在哪里,却不见人。过马路问花店的老板,说刚才还在,要我等一会。又告诉我前面拐弯处还有两家。
那块牌子让我好奇,我决定等。不想站在马路上吃灰,我进了做蛋糕的铺面,站在玻璃后观察补鞋摊子。一刻钟后,看到一个穿黑衣黑裤的老人,戴一副眼镜,在往三轮车上搬东西,我估计这老人应该是邓师傅了,于是过去。
我还没走到摊前,邓师傅又走了,我喊住他,提了提手中的鞋子,示意要修鞋。邓师傅说他还去搬点东西,要我再等等。我走近三轮车,看到搬过来的东西是两箱啤酒瓶,上面还有一小捆报纸,一把锈渍斑斑的菜刀。
一会,邓师傅一手提了一个老式的煤球炉从一栋刚刚搞了外装修的六层小楼出来,看他走路有点吃力,我过去想帮他一把,邓师傅说别弄脏了手,拒绝了。我问他要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他说有用,做饭烧水烤火,用处大。好像是怕我认为他占小便宜似的,解释说送东西给他的人修了两双鞋,他没收人家的钱,人家送了这些废品作回赠。
收拾后,邓师傅才坐到摊前。我把鞋子给了他,他看了看说:这鞋不好补。我说你是八级工,应该没问题。他抬头望我,目光从老花镜上面出来,一眼的自信说:不是和老板吹年,我搞这一行四十多年了,什么疑难的鞋,到我手上就服帖了。说完自个乐了,这乐有满足,也有些狡黠的成分。
邓师傅抽出鞋垫说:老板,这鞋有点高档,我得细心点,二十块钱,要得不。我说要得。邓师傅要把线扎在鞋沿上,我要他扎在鞋底。扎鞋底的话,线要从鞋的里子出来,不怎么好操作,邓师傅觉得有点费劲,想加工钱,嘀咕说:要是这样,别个三十块钱也不做的。我说做生意讲的是诚信,你答应了,就要兑现承诺。
邓师傅没多说什么,用小刀在鞋底上切一条线缝,做着这些时,不时和我说话。我对他的八级工感兴趣,问他是哪个部门核定的,他嘿嘿笑着说:自己给自己定的。怕我是哪个政府部门的人,停下活计,正经问我:写下这个,不违章法吧?我说给自己封十级工,也不碍事。邓师傅哈哈笑,说:老板,你真懂我,开始我准备写十级工的,我就不晓得有没有十级工。
邓师傅说第一句话时,我就听出来他是湘乡人,他也听出我是双峰人,我说我是娄底娄星区的,他说双峰有几个人也在长沙搞修补,他认识,说话的声音和我一模一样。我问他一直在长沙搞修补?他说从七几年就来了长沙,我说赚了不少钱吧,他说讨饭的行当,哪像你们当老板的,一天抵我们一个月。我说我也是讨饭的,不敢和你比。他乐了,说:不瞒老板,要说没赚钱,那是说假话,但赚的是个辛苦,是个日晒雨淋,是个低三下四,这碗饭不是人呷的。不做又不行,我们农村人,一没靠山,二没文化,三没资金,只能盘下个讨饭的活。四十多年,刮风下雨,下雪下刀子,我天天坐在这树下,我堂客帮人家做做卫生,带带小孩,靠我们老俩口辛苦赚点钱,把三个孩子送到大学毕业,九六年又把老家的房子重新砌了,只是房子是砌了,没怎么在屋里住。
聊着聊着,邓师傅放下手中的活,一跃跳起来,往马路对面的饭店小跑过去。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原来是饭店搬出几个纸箱丢在垃圾桶附近,邓师傅小心将纸箱里的肮脏物清理进垃圾桶,提了纸箱又小跑回来。难怪邓师傅在修补时,满眼四路子溜,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习惯性的,这才知道他是在观注这些事,而且,在我修鞋的过程中,他三次起身去了不同的地方捡回纸箱。我问邓师傅平时兼顾收些废品?他说现在生意不像以前好做了,闲着也是闲着。我指着他摊前的鞋子,说生意不是挺好的么?邓师傅也学会了新名词,他说了一个一次性消费。他说高档的,不会到他这里来,一般的,又是一次性消费,坏了再买新的,不怎么修补了,就连他小孩子们的鞋子,坏了也不送给他来补,他现在的日子,只是勉强糊口了。
邓师傅的手被针扎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了他的双手。这真是一双做事的手,粗糙,开了皲,黧黑,像有一层油渍干了洗不掉,指甲也不修剪,里面全是黑渍渍的东西。一位老妇人过来取鞋,邓师傅接下老人的五十元钱说:你这鞋之前肯定不是在我这里修补的,我没有这样差的线。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钱,全是一张张皱巴巴的块票。邓师傅抽出几张后又把钱塞进上衣口袋,然后掀开衣服下兜,腰带上有一个小袋子,拉开拉链,取出一叠钱,全是十元一张的,理得整整齐齐。邓师傅抽出四张给了老人,把钱原封放进袋子,拉链锁了一半,又拉开,把钱拿出,拿了老人的那张五十元的票子,放在眼镜下仔细瞅。我说不会是假的,邓师傅不好意思笑笑,小心将钱塞进袋子,又仔细摸了摸,发现妥当了才继续做活。
邓师傅的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我爷爷也是手艺人,只不过比邓师傅干净,不要日晒雨淋。我爷爷也吃了许多的苦,去世时,那双手又瘦又黑,看到邓师傅的手,我就想到了我爷爷。邓师傅比我爷爷小,今年才六十五岁,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老大老二都是女孩,一个在广州当老师,一个在长沙打工,最小的是男孩,也在长沙做点小生意,日子也能过下去。邓师傅和老伴租了个二十平米的房子,每月六百元,水电加杂七杂八的费用五六十块钱,他要人家的煤炉,就是想买煤来烧,便宜,可是他并不晓得长沙限煤了,买不到煤球。邓师傅的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儿孙满堂。我问邓师傅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他说农村人闲不住,还说小孩子们有他们的难处,趁现在还动得,攒个养老钱。
一只鞋补好了,邓师傅要我看看。他说另一只鞋不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一来鞋子没有坏,不需要补,二来这鞋太难补了,又把前面说的三十也不接的话重复一遍。我虽然觉得邓师傅没讲诚信,但还是理解他。另一只鞋的确好好的,我想的是,我家小伙子天天和水泥打交道,难免不坏,反正要弄的,不如一次弄到位,坚决说没坏也弄。
对面有人熏腊肉,喊邓师傅过去帮忙,邓师傅要我等等,过去了。回来时,手里拿了十来个铁勾子,人家腊肉熏好了,勾子不要了,邓师傅做废品捡了回来。邓师傅双手在布兜上搓了搓,不情愿的拿起鞋子前后看。我知道邓师傅真是不想补,也理解手艺人的苦处,说:加十块,你帮我认真做好。邓师傅二话不说,接过我的钱,拿小刀在鞋底上划线,然后默默做着活。
流浪汉
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跟踪这个老人,不是因为他穿得精致,给人的印象像一个知识分子,而是源于我某天的早上和下午在阳台上两次看到他在同一个垃圾桶里翻东西。原以为他只是捡些破烂,这种老人我经常见,他不是,他在捡吃的或用的。我看到,一个上学的小朋友将一根吃剩的油条随意地丢进垃圾桶,老人几步走过去,从桶里拿起油条,转身就吃起来。
一开始,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有一次,我下楼替我孩子买早餐,我碰到了他,只见他手里大包小包全是报纸矿泉水瓶易拉罐,一个塑料碗里装了半碗干面,中指提个塑料袋,里面有几个变了色的香蕉,几个有点发霉的橘子,一小节甘蔗。显然这是从不同的垃圾桶里捡到的。老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并没有反应过来,当老人慢慢从我身边走过并有一股异味进入我的鼻息时,突然想起他是我在楼上看到的那个老人,于是,我返身跟了上去。
我和老人打了招呼,他并不理睬我,有点莫名其妙的望着我。我一边跟着他走,一边小心翼翼想一些不至于让他难堪的话问他,老人还是不搭理我,只是加快了脚步,想与我保持距离。那几天非常冷,老人戴着鸭舌帽,穿一件银灰色羽绒衣,一条灰白的牛仔裤,我原来也有一条这种裤子,十几年前买的,现在很难从市面上看到了,一双派克旅游鞋,很干净整洁。老人的年龄大约在六十五岁上下,五官端正,棱角分明,戴浅色近视眼镜,偏瘦,肤色偏白,留胡须,但修剪得整齐,要不是手上提着这些垃圾,我想到了我过去杂志社的同事廖老师。
我知道老人从心里拒绝我,不再纠缠,想着老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不会神经有点问题,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我还想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索绕着我,想解开。
一段时间里,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阳台,望着路边的几个垃圾桶,我在寻找老人,看他有没有来捡垃圾。遗憾的是,守了几天,并没有看到老人。
半个月后,单位搬迁。某天清早,我去另外一条线路搭车,路过邮局前面的小花园,看到老人坐在花园里看书,神情十分专注,我本想打招呼的,停下脚步想了一下,还是走了。走时回头,见老人继续埋头看书,想他并不善于与人交流,也许,他压根就不想与人交流。
连续几天,我都看到老人拿着同一本书,坐在花园中的同一个位置,专心细致地读着书,我忍不住了,上前和老人说话,我问老人是哪里的,为什么每天那样早就坐在这里。老人放下书本,木纳地望着我,却不回答我。我还是一脸的微笑,问老人吃早饭了没有。老人这回站起来,拍了拍屁股,然后朝南边和北边方向望了望,选择往南边去了。望着老人的背影,我摇摇头,自嘲地笑了。
一个多月看不到太阳了,这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沿街满是晒太阳的男女。因为有事拖到下午才去单位,路过一地下通道时,看到老人坐在通道出口的石台子上晒着太阳,看着报纸。老人没戴帽子,才发现他头秃顶了,一绺长发从左边绕过头顶,将没有头发的地方盖住,而且头发已经花白,也显得干涩。老人的衣服是敞开着的,里面穿一件天蓝色毛衣,还是那头灰白的牛仔裤,只是裤腿是往上绾着的,脱了袜子,光着脚踩在鞋子上。
估计老人是晒了一会太阳了,他的身边有一堆报纸,有快餐盒和筷子,有矿泉水瓶。我佯装打电话,喂喂的喊了几声,在出口来回走动,有意无意说车子到了什么地方,又说那我在某地地下通道出口等,一切很自然的在石台子上坐下。
我装做才发现老人,和他打招呼:又碰到您了老人家。第一遍他没抬头,到第二遍时,他面无表情点了一下头。只要他点头,我就能让他说话,那点头的动作让我判断老人意识是清醒的,于是我问他:老人家,经常看到你在这一带,你是住在附近么?
老人用手去抓了抓脚指头,又改用右脚底去搓揉脚指头,并继续看他的报纸。老人还是不搭理我,我不想放弃,又问:老人家,我看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隔一会,我又问:老人家,您今年高寿?家里还有些什么人?老人始终不抬头,目光也不移开报纸,但我发现,他似乎有些躁动不安,双眼一直在游离,最后,将衣服上的帽子搭在了头上,把头包裹住,只露出鼻子和嘴。
平时下班,我坐同事的车回家。前几天,同事休年假,我坐在伍家岭北下,过地下通道时,发现老人睡在地下通道里。老人的睡处,靠墙摆了十来个包装袋,是一些衣物和被子,其他全是捡回来的垃圾,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其中有一个透明的塑料包里,全是杂志和书,一床被子紧贴着墙铺开,老人用一个包裹当枕头,躺在被子里看书,他的脚那头,还有一个流浪汉在吃捡回来的东西,有半边西瓜显得有点邋遢。
我站了一会,并没有和老人打招呼,返回去,在入口那一头,有一个卖卤猪脚卤鸡爪和卤蛋的妇女,我买了二十块钱猪脚和鸡蛋,要给老人。老人不接我的东西,眼睛也不离开书,我对他说:“睡在这地下,晚上不冷么?”脚头的那个流浪汉回答:习惯了。我打开盒子,要流浪汉自己拿半边猪脚,流浪汉呵呵的笑,拿了半边,还拿了一个鸡蛋。我问流浪汉认不认得老人,流浪汉说他才来一天,不认得老人。又说老人不欢迎他来。
我把东西放在老人头边,悻悻的走了。走到出口,有一个小姑娘在卖雨伞及女孩用的小商品,本来已经上梯子了,又回到小姑娘的摊前。我问小姑娘认不认得那老人,小姑娘说认得,我问她老人是不是精神方面有毛病,小姑娘说有点。我问小姑娘知不知道老人的一些情况,小姑娘说知道一点点。
于是,从小姑娘那里了解到了老人的遭遇。
原来,老人姓钟,湖南某地人,六十三岁,是一名园林工程师。有妻子,有儿子儿媳,还有一个孙女。多年前,当地拆迁,要拆他家的房子,因补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成了钉子户。他唯一的儿子,在拆迁过程中和拆迁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被拘留了几天。出来后,准备了一瓶农药,说谁拆就死在谁面前,想以此获得想要的价格。不料阴差阳错,医院途中死亡。从此老人辞了工作,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北京,省里,省里,北京,几年的辛酸和屈辱,我不能用文字表达,我怕说出来,没人敢发我的文字。
小姑娘还告诉我,老人在这个地下通道里住了二个多月了,平时在附近捡些垃圾,偶尔会在公用厕所里洗个澡,洗洗衣服。也有好心人送些吃的,老人并不接收,放在他身边,过后老人也会吃。小姑娘说,老人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了,家里人也没来找过他。
我问小姑娘,老人是不是从来都不和人交流说话?小姑娘说是的,她也是前段时间才和老人说上话的。前段时间天天下雨,老人出不去,小姑娘给了老人一把伞,老人回来后要把伞还她,小姑娘说送给老人了。老人收下了伞,小姑娘趁机和老人聊了一会,才知道了原委。
前几天,我在家搞卫生,偶然翻出了一件军大衣,快二十年没穿了,早几年搬家时我就想送人的,因没人穿,没送出去。我想起了老人,拿了大衣奔地下通道,到了才发现,老人搬走了,摆地摊的姑娘和妇女也不见了,想是城管让他们搬走了。
之后,我再也没见到老人。
夫妻环卫工
我经常走的那一段路,连接着一座破败的高架桥,因为设计不合理,加上附近拆迁,三天两头堵车,沿路到处是垃圾和纸屑,给人脏兮兮的感觉,很不舒服。
我常常看到一个老人,推着一辆垃圾车,拿着专用的工具,在这条路上不停地清扫,附近拆迁给老人带来了一些困难,尘土飞扬,前面扫干净了,后面又脏了,返回去重新又扫。特别是堵在路中的车,总有些人往外丢垃圾,老人在车辆中绕来绕去,将烟蒂槟榔渣橘子皮逐一扫尽,面对这些人,老人没有一句怨言,只是默默的做着他的事。
有天中午,和同事外出吃饭,因担心桥上堵车,就走桥下。当时是八月,长沙的八月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室外温度达到41-43℃。在桥和地面呈45度的位置,我看到了老人的垃圾车,老人坐在垃圾车下,背靠着垃圾车的轱辘,在看一张报纸。我想拍几张照片,让同事停车。
我早认得这个老人,老人也认得我,以前碰面时总要和他说一会话,问问他的情况,老人也会如实告诉我。老人姓彭,湘潭人,68岁,家住农村,两个女,一个崽,也都在农村,前些年,崽女们去了广州打工,混得不好,没攒下什么钱。这些年,广州也不景气,加上孙子孙女们大了,要回来读书,于是,崽和女都回了老家。崽在村里盖了房子后,欠了账,所以他和老伴才出来找事做。老人的老伴66岁,也是环卫工,就在前面的路上,和老人中间隔了三段。老人原来想和老伴扫同一段路,环卫局不同意,说是有规定的,一家人不能在同一组。
我拍了几张照片,就是想有一天写他点文字,可惜后来照片不小心被我删除了。
那天,我把吃剩的菜打了包,还特意盛了一盒米饭,我说要送给老人,同事很赞成。我们沿路回来,老人还在原地,只是他在车轱辘上睡着了。老人的睡相看起来很疲倦,一顶破旧草帽坐在他屁股下,报纸还抓在手上,手搭在膝盖上,头往一边偏下,显然,老人是看报纸时睡着了。老人头发苍白,稀疏,汗从他鬓角流出,一直流到脖子。老人睡得很香,均匀的鼻息,隐隐约约,桥上车来车往,桥下也陆续有车经过,都不能搅醒老人的梦。
我不忍心叫醒老人,让同事先走,说一会走路回去。我到单位只要三五分钟,整天呆在空调房里,出点汗也好。
老人的时间是不分休息吃饭的,只要路上有垃圾,就要随时清理,局里每天有人上路检查,发现不干净,要扣工资。环卫工一天三班轮,早班5:30到11:30,中班11:30到下午5:30,晚班5:30到11:30。环卫工人的工资也不高,早几年,每月一千五百多元,扣除各项保险,到手的也就一千多点。后来逐年增加了点,老人今年的工资是一千八百多元,扣除各项保险后,发到卡上的有一千五百多点。我问老人早过了退休年龄,为什么还要扣保险,老人说他也不清楚,好像是一些意外伤亡之类的险种。
我呆了一会,老人醒了,要起来去做事。我把东西给老人看,说带了点剩饭剩菜,问他嫌不嫌弃,一再解释干干净净的。老人一脸的笑,也有点不好意思的味道,说:不会不会,难得你老板想得起我。老人千谢万谢接了东西,在垃圾车上望了又望,我晓得他是在找存放的地方。垃圾车的把手上,老人放了一块木板,固定好了的,摆放了一些纸箱啤酒瓶之类的废品,老人将饭菜小心放在上面。我担心气温太高,饭菜会馊,提醒着老人,老人也觉得会馊,却没有主意。我问老人吃了饭没有,要是没有的话,不如就吃了。老人说他出来带了馒头咸菜,已经吃过了。我看到前面有商店,想那里有冰箱,建议老人不如寄存到商店里。老人有点担心,说会给人家添麻烦。我说不会的,要帮他送去。老人说:还是不麻烦人家,饭菜的气味会坏了人家的东西。
老人决定送回他住的地方,我问远不远,老人说不远,七八分钟路程。我突然想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向老人提出来,老人也不反对,只说经不起看。
老人住的地方是一个公用厕所,过去进厕所是要收费的,有间小房子。后来不收费了,小房子空下了,老人找了关系,才租下这间小房子,每月三百五十元。房内摆了一张床,说是床,不如说是一个席梦思,是老人捡来的。席梦思是单人的那种,下面用砖垒起来,一块床单盖了一半,露出了并不整齐的砖块。墙角有一个旧冰箱,老人说是花一百块钱买的。老人将饭盒放进冰箱,我看到,冰箱里除了一些并不整齐的蔬菜,只有几个鸡蛋,还有一个盖了盖的碗。凭我的观察,那些蔬菜肯定是老人在菜市场捡来的,本想问一声,却问不出口。
屋里除了这个冰箱和一个旧电饭锅外,没有任何电器,我想,那电饭锅只怕也是捡来的,问老人,果然是。
我一直想见见老人的老伴,因为太热了,就放弃了。有次,帮了朋友一个忙,非送一张消费卡给我,推不了,也就接了。消费卡有时间的,眼看要过期了,和老婆去了指定的那家商店购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出来走在路上拦车,不小心将东西掉在地上,顿时香油瓶酱油瓶调料瓶砸个稀巴烂。老婆怨我做不得事,我也一脸无奈,沮丧说把路弄脏了,不晓得要如何收拾。在我懊恼的时候,一个环卫老人提了工具过来了,她一边安慰我老婆,一边清扫地上的玻璃。我感谢了环卫老人,帮她把东西捡进垃圾箱,老人要我别动手,说容易划了手。
我突然想起了老彭,问老人认不认得前面的彭嗲。老人说那是她老公,我说你就是彭嗲的老伴啊,老人问我认得她老公?我说认得。
老人的心态比老彭好,喜欢说话,一说就要笑,略胖,比老彭显得年经。闲扯了一会,我问老人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好好在家养老。老人说:耍也是耍了,趁现在动得,能挣一点就挣一点。又说:我这人,耍也耍不住。老人似乎还得意,说她和老伴每月有三千多元,她崽媳妇在家还没有他们挣得多。我问她做得还习惯,老人连连说习惯。我问她还要做到什么时候,老人说:不晓得局里怎样想,要是局里允许,想一直做下去。不一会,话锋一转,说:也讲不清,做这一行,辛苦不要紧,时间长也不要紧,没地方休息也不要紧,就是安全没有保证。老人说完,深深叹息一声,告诉我说前一阵子,她的一个老乡,早上五点多钟在扫马路,被一辆高速开过来的汽车撞飞了,当场就死了。
对于安全,我是懂得的,经常看到电视中报纸里讲哪里环卫工人被汽车撞了,被人打了。虽然气愤,却离我远。此刻,望着老人失落的样子,无从安慰,只好要我老婆拿些东西。老婆选了一袋墨鱼,一包红枣,要给老人,老人却死活不肯收下。
街道栖居者
在单位没有搬家之前,我都是走路上下班,要从一座立交桥下经过,总会看到沿路并不规则停着七八辆微型面包车,微型车的后面,停着一辆类似于皮卡车模样的小四轮,上面摆了大锅,水桶,胶管,杂七杂八的工具。从早晨到晚上,车辆一直停在同一位置,好像那里是他们的专属区。如果有交警过来驱赶,他们会开到别的地方遛一圈,又开回来。这是一些专门从事屋顶补漏作业的人家,车身广告上写着:屋顶补漏。
正副驾驶室内坐着的,一准是一男一女,都年轻,二十六七岁,或三十岁,有的还抱着一个孩子,一二岁,男孩女孩都有。显然,这是一家人,年轻男女是一对夫妻,男孩女孩是他们的孩子。也有一二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和某辆车的年轻人在一起,从长相判断,显然是年轻人的父母。
从车牌上看,这个群体来自安徽。
我每天早上路过时,看到车前摆一桶水,女的蹲在路边漱口,或梳头发,或坐在车里吃早餐,早餐基本上是这几样东西:油条,面包,馒头,偶尔也会吃碗粉,或小笼包子。要不在洗衣服,因为缺水,衣服淘只一遍,随便找几棵树搭上。有很多次,我还看到女人们合起来在一起洗头,相互帮衬,有说有笑,叽叽喳喳,好不热闹。路过的人稀奇地看她们,女人们感觉到了,虽然有些羞赧,却也习以为常。
要是到了中午或晚上,女人们便在车旁架起了锅灶,车上有煤气罐,有煮饭菜的全套家具,瓶瓶罐罐。切菜的砧板就摆在路边石基上,碗筷放在桶里,有的在附近捡了块三合板,搭成个小桌,有的则将炒好的菜放在地上,吃饭则像工地的民工,蹲着,或坐在车里吃。菜简单,香干炒辣椒,小豆芽。偶尔加个荤菜,给小孩子吃。
这些人没有租房,吃喝拉撒全在车里。不是天天有事做,一个月里做得五六天活,实属不易了。不做事也不能乱走,一是没地方可走,二来怕有人来拉活,不敢走开,就天天坐在车上,男的看手机,或看电视,车前都有一个小平板电脑。
我看到,他们都很无聊,相互之间也没有交流,不是坐在车上发呆,就是睡觉,他们的目光不敢和过往的路人对视,他们心底明白,过往的行人从心里瞅不起他们,因此,他们从不和任何一个善意的眼神交融。
有一个男孩,浓眉大眼,高高大大,很像我新兵连的班长马子新。我一直在寻找我的班长,只要碰到安徽人,我都会主动打招呼,问人家姓什么,安徽什么地方人。我问这男孩姓什么,他说姓吴,我一听有点失望,问他们这些人里有没有姓马的,他说没有。但是说他们村里有许多姓马的,我问认不认识一个叫马子新的,他摇头说不认识。那对五十来岁的老人中,有一对就是小吴的父母,还有一个车里的一对夫妻,是他的妹妹和妹夫。小吴的妻子不过二十二三岁,长得挺漂亮的,有一个男孩三岁多了,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我也见过,因为小吴妻子又怀孕了,把男孩送回了老家,交给外婆带。
小吴不做一点“家务”,所有事情都是他母亲做,小吴的妻子在一旁打下手,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样子,倒像是一个家,只是,这个家是在马路上。因为有孕妇,每餐弄了一个荤菜,偶尔也见小吴喝瓶啤酒。
认得小吴之后,慢慢和他熟悉起来,走过时总要打声招呼,我也邀请过要他去家里玩,答应得利索,却从不进我家。我知道,他们是不想打扰我的生活。
进一步接触后,更多的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每天,五点钟就醒来了,被那些早起忙生活的人闹醒,不能懒在床(车)上,要立即起来,在人少时穿好衣服,还要找个地方方便了。我问怎么方便,小吴说小便就在花草中解决,大便就去前面的宾馆。好无聊挨到六七点钟,洗漱,吃早餐,等拉活的人来。有活,去干活,没活,一天呆在车上,哪里也去不了。晚上六七点就上床(车)睡下,却睡不着,太炒了。夏季还好点,可以在路边坐到凌晨一二点,也可以睡在立交桥下的石板凳上,到了冬季,天一黑,外面冷,只好上床。洗澡更是成问题,男人还好说,提桶水随便在哪里搓几下完事,女人要等到夜深人静时,找一个隐蔽处洗,男人在一旁提一块布遮拦一下。
一年中,他们有两次回老家,一次是八月中秋,一次当然是春节了。一到暑假,他们都会把自己丢在家里的孩子接来玩一个假期,孩子们好像习惯了这种生活,白天就在立交桥下的空地乱转,晚上和母亲睡在车上,父亲则睡在外面的石凳上。
暑假,既是孩子们高兴的日子,也是大人高兴的日子,终于可以有一段短暂的时光与家人相守。孩子们围着车子转圈,大人也跟在孩子的屁股后面,生怕孩子摔倒,或是被过往的车辆撞了。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尾气尘埃,孩子们陪父母坐地马路旁,任陌生的人从他们身边走过,眼里却满是稀奇,茫然。我常想,长大后,孩子们还能否记住,曾经有过的这一段时光?
有天周末,我去买菜,顺道去了小吴的车子,我坐上了他的车,和他聊了差不多一个上午。我主要的是想看看他们的“床”。说是床,其实就是把微型车的后座拆了,焊了一个架子,上面放上一张木板,固定好。微型车空间本来就小,还塞满了东西,恰好够两个人的空间,还不能乱动,车窗是密封的,一点不透气,憋得狠。
我想到了一个字:性。我想弄清楚他们的性生活,和小吴隐密的提到了一点点。小吴聪明,知道我想要知道什么,毫不隐瞒说:说起来不怕你笑话,过夫妻生活像偷人一样,想要了,也得等到半夜三四点钟,还担心有人会路过,不敢有一点动静,慌里慌张的,没有一点质量,更谈不上享受。小吴说:有天晚上,他醒了,想要,和妻子正温存时,一个醉汉在他的车子边不断呕吐,吐完了不断骂娘,对他的车又是踢,又是擂,吓得夫妻俩不敢动弹。明知有人砸他们的车,还不敢出面制止,忍气吞声,生怕惹出祸来。
小吴一家的日子,并不只是这一点酸楚,但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隐忍,不得不舍弃他们的生活质量,因为,给房屋补漏,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
算命先生
几根棍子,几个挎包,匆忙的脚步,慌乱的神态,忐忑的心情,构成了一个姿势:牵羊羊。这是光明人眼中的风景,殊不知,天下人都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风景。
其时已是正午,阳光如一盏白炽灯照在人们头顶上,各种遮阳的工具五颜六色。远处的树荫下,一堆搬运货物的民工挤在一起,马路上,隐隐约约看到往上升起的焰子像跳跃的水帘。我刚从对面的东北水饺馆里吃完东西,正要急匆匆赶回大厦里的某间办公室,躲进满是冷气的空调中享受现代化带来的那份舒逸。就是在这个时候,这六个人正好从我眼前过去,他们身上背着二胡、背袋,还背着一个小马扎,左手搭在前一个人的肩上,右手拄着一根竹棍,想要走过马路。还是红灯,车辆如赶集一样跑得狂欢,喇叭声声声入耳,催命似的让过路的行人更加躁动不安。盲人中的第一个用棍子不断地在前方探路,眨眼的工夫,棍子被急驰而来的一辆丰田车辗压过去。我心一惊,连忙说是红灯,不能过。六个人齐声说谢谢,我却感到脸突然火辣辣的。
在绿灯亮起来的时候,我迅速走到他们前面,引导他们走过马路。我问他们要去哪里,其中一个说去做事。我没说话,望着他们就这样从我眼前过去,直到慢慢的消失在满是水帘的尽头,才悻悻的离去。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我更不清楚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有一点,我应该知道,他们肯定不是一家人,他们走到一起,肯定有许多的故事。还有一点,我是很想知道,这些人做事的地点在哪里?他们的生活境遇怎么样?
走在前面的,那个小的,我看不出他有多大,或许是二十多岁,或许是三十岁。走在他后面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我估摸着有七十多岁了。那位唯一的妇女,走在中间,腰上扎一条丝巾,把东西紧紧系在胸前,生怕有人从背后抢了她的东西。妇女的脸上露着笑容,她是高兴的。她为什么高兴,我并不清楚,或许是因为她有希望,或许是因为她怀揣着希望,或许是因为她已经带回了希望;她也是放心的。她放心,是因为有人保护着她不受到伤害,她前面有人引路,她后面有人断后,哪怕世界是黑暗的,她也不需要害怕。而走在最后的那一位,看上去四五十岁年经,是这六个人中最高的。此刻,他的表情是凝重的,他的竹棍一样在地上敲敲打打,还不时两边观望。其实,他什么也望不见,他的观望也许是习惯性的,我揣测他的眼睛之前是能看得见的,他手中的竹棍告诉我,他除了断后,还是这六个人的保护者。
我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年龄,也不需要知道他们是不是一家人,更不需要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我只需要知道,这是一些社会上的弱者,是一些需要我们特别帮助和关爱的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不是乞讨者,他们是一群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为什么这样说?看看他们自带的东西,一条小马扎,是坐的,也许在某一个涵洞,也许在一座桥头,某一处阴凉地方,或者是在某一喧闹商业区或居民区,总之,是在有人经过有事情可做的热闹地方。一把二胡,形状大小不一,却直观的告诉了我,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没错,他们是一群算命的,他们的工具十分简单,一些纸牌,字符,罗盘,或脸相和手相用的书籍。他们一整天坐在那里,等着有人上前问话,搭讪,然后根据顾客的需要,说着一些投机取巧的话语。这就是他们一天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虽然有点投机行为,但市场需要,客人需要。他们做了市场和客人需要的事情。
我有时候想,人在享受他们的投机话语时,心里却在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其实,我们在歧视他们的同时,却在不自觉的拷问我们的灵魂。
我想到了一些词汇:干净,肮脏,猥琐,倜傥。等等等。但我不知道,这些词哪些适合于我们,哪些又适合于他们。
因为有了那一次的邂逅,我便开始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biyadia.com/bydsc/9959.html


